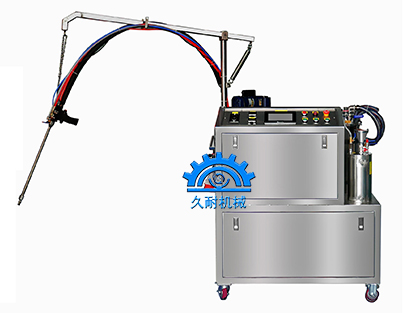他离开了潮湿炎热的梅州农村,离开了机器轰隆作响的流水线,离开了遍布厂区的城中村。各路策展人、艺术家,或别的一些“下沉品牌”,因为他身上“杀马特教父”的标签找上门来。
发型依旧是他最大的武器。作为杀马特家族中极少数破窗的人,这个“遗族”现在思考的是如何设计出更有料的发型吸引观看。而更多的杀马特早已剪去长发,消失在公众视野。他们中的不少人,仍然在产业转移和城市化进程的末端漂泊,流转在单行道上。
我们站在被粉紫色光束晕染的溜冰场外,空气中弥散着模糊的烟味。罗福兴身处溜冰场的正中心,全部头发被分成10束,用发胶强力拉升,耸立、巨大、像刺猬、海胆,或某个漫画里的人物。他涂着深色口红,面对镜头和打光板,不断切换表情和动作。电子音乐的混声中,临时组建的“家族”成员们的溜冰鞋划过地板,发出脆响。
这是罗福兴和一家服装品牌合作的物料拍摄地。拍摄日期定在5月下旬,为期三天,住宿标准限定为400元每天,拍摄地点贯穿街心公园、溜冰场、地下酒吧。他穿脱了好几套衣服,指指一件印着他大头的联名款T恤衫,爆了句粗口,“太傻了”。
脱下了溜冰鞋的罗福兴甚至是瘦小的。他说自己隐藏着六块腹肌,是每天早晨七八点跑步一小时的产物。收工以后,这颗由蓝绿色向暗红色渐变的刺猬头,出现在上海静安区洛川东路路口。他坐在溜冰场楼下的台阶上,尖锐的发型棱角像要刺到暮色里。正是下班时间点,行色匆匆的路人惊异地回头张望。罗福兴扬起嘴角,对着路人比出剪刀手,或者一颗爱心。“现在‘社牛’了,”他自嘲说。
他频频挥手,向当天参与拍摄的几位上海本地志愿者告别。她们都带着小众精致、价格不菲的服装和道具。一个皮肤白皙的小姑娘顶着半扇彩虹头,另一位2003年出生的小姑娘将短发扭成两个尖角立在头顶,“我自己设计的,因为我觉得很像小恶魔和杜宾犬”。
“小恶魔”向我们介绍,自己也是一位亚文化博主。拍摄当天,她在朋友圈发布了罗福兴的视频,配上了“教主好帅”的文案。
而“教主”却看不懂00后们的“Y2K”和朋克风格的打扮,他不明白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怎样的亚文化,就像他也无法准确描述当年的“亚文化”杀马特:“能够说是个发型,能够说是文化,你也能说它是个社群,社群里面产生了一堆自己的文字、语言、发型、着装、审美,包括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爱。”
“教父”罗福兴讲述的起点里,他打工的深圳,就像溜冰场的灯光一样让人眼花缭乱,但未成年的他被困在庞大的机器和灰暗的厂区里。他在一些非主流家族的QQ群里获得情感认同,随后开始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明星石原贵雅,因为他的造型看上去“很牛X”、“很有冲击力”。2006年,他烫了一颗红色的爆炸头,上传到网络上。
他将这种风格命名“杀马特”,为自己在创建了“杀马特创始人”的词条。杀马特,是英文“smart”(时尚的、聪明的)的音译,符合罗福兴想要的“酷炫牛X”。当时他一直以为英语字母和中文拼音类似,“‘tiger’就是泰戈,‘teacher’就是踢车,我一直是这么记单词的,我们那的英语水平就那样。”
通过QQ群,杀马特家族迅速扩张。如果不是后来那场从线上蔓延到线下的“围剿”,杀马特最鼎盛时,罗福兴掌管着几十个群。据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博士王斌统计,截至杀马特活跃末期的2014年底,百度搜索以“杀马特”为主题的网页将近1700万,杀马特贴吧累积发帖近150万,活跃的QQ群不下200个。
杀马特最流行时,石排镇名流美发店的老板小天不接剪头发和烫染的业务,一天就做百来个杀马特发型。晚上九十点后,工厂收工,等待的工人们坐在对面超市门口的椅子上,小天做好一个,就向外招手,示意下一个进来,美发店要营业到晚上十一点半。
小天不确定谁才是杀马特教主,他眼中的杀马特是一群人,他们常常会三五个聚在一起,拿着放着歌的录音机“炸街”,或是扛着溜冰队伍的旗帜,“唰”地从石排公园口滑过。
罗福兴清楚,他在上海的拍摄,是在“表演”杀马特,复刻的是一个业已消逝的场景——工厂、溜冰场、理发店,这些曾是杀马特们打工世界里的全部。
“上海有海吗?有没有能看到海的地方?”在来上海拍摄广告之前,罗福兴在电话里问我。
五岁那年,千禧之初,父亲给他过了唯一一次生日,买了一瓶可乐和一个5块钱的面包,带他去深圳金沙湾玩。这是他童年记忆里为数不多的来自父亲的陪伴,也是他对大城市的第一印象:“最牛最厉害的、最让我感到震撼的,就是大海一浪一浪接过来……”
罗福兴出生在广东梅州五华县的一个农村里,“四面都是山,只有小溪”。青壮年外出打工,祖辈和孩子留守在村子里,是这个广东经济最落后的城市里的常态。罗福兴曾多次在采访中提起父亲“在外打工”、“有3个老婆”、“不寄钱回家”,而被隐没的母亲则在他和两个妹妹年幼时留在梅州,一边打工一边拉扯三个孩子。不久后,母亲也前往深圳。他像一个皮球一样流转在祖辈家中。偶尔见到母亲,打骂也远多于温情。
罗福兴不爱读书,但他很喜欢美术课,画画成了他当时唯一认真去做的事情。他看着农村屋里的挂画、门前的对联,画的最多的是龙凤和荷花。“因为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说很有成就感,有时候领导评奖,还能拿第一名或者第二名。”他发现一直以来被忽视、被打压着的自己,原来也能出班级的黑板报,也能把名字写在荣誉榜上,尽管他回看,当时“画得比较烂”。
“我们那里没有艺术细胞的。”罗福兴用“贫瘠”来形容梅州山区,“可能是环境问题,包括教育(问题),大家都不读书了。”12岁的罗福兴跑到深圳的一家微波炉厂打工,操作一台有他两倍高的日本进口二手注胶机。“机器比人金贵”,他听说这台机器价格要好几十万,让老板在厂区里格外有排面。每当有管理人员或领导来检查,这帮瘦小的黑童工就躲进厕所,扒拉门缝听外面的发言,间或,掌声响起。
杀马特是一群什么样的人?罗福兴熟练地回答,“都是农村来城市务工的,在城市和农村夹缝中的人。”
“杀马特”家族创建以后,在线下的厂区,杀马特通过发型互相辨认,像一个暗号。而线上,他们自称为“杀马特贵族”,以“韩”、“安”、“泪”三大姓冠名自己。他们熟练地运用着火星文或炫彩的文字,统一格式的角色标签下,“皇族”“部落”里的“伯爵”和“女帝”隐藏了各自的家庭背景和生存环境,通过互相夸赞彼此的造型,抑或是共同的幻觉来交友。
2011年,17岁的阿梅看到工友们都换上了颜色样式各异的发型,也偷偷去美发店里做了个黄色爆炸头,因为黄色“明亮好看”。理发店似乎成了工人们在漫长的工时之后重新找回自己的场所,只需花个几十块钱或者买瓶发胶,就可以把头发支棱起来。他们拿着从QQ空间下载的图片或者别人的照片,或是腼腆地表示,怎么做都可以。
在小天看来,来做杀马特发型的,大多数是一群“温和老实”的产业工人。有人只剩下三十块钱,全用来做杀马特发型;有人全身上下都臭了,做完发型又能自信地抬起头;有的工人犹豫再三,向小天提出,能不能赊账。
2016年,抱着寻找中国本土“朋克文化”想法,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李一凡筹拍纪录片,开始寻找杀马特。他在开拍后发现,与预设的那些知识分子解读大相径庭,和罗福兴、阿梅类似,“杀马特”主体是90后年轻人,他们大都出生于欠发达地区,当过留守儿童,并在小学和中学辍学。接受媒体采访的杀马特们,第一次去工厂打工的平均岁数是14岁,最小的12岁。在制造业野蛮生长的时代,有人每天打成千上万个螺丝钉到凌晨一两点,有人做百洁布,手指甲都被磨光了。
有人评论,杀马特的历史,“是半部血汗工厂史,也是半部城市化史。”杀马特是一种发型,也是这群产业工人的铠甲,仿佛刺破天际的发型与结伴同行赋予他们勇气。他们不再是流水线上等待盘剥的廉价劳动力,即使不像社群中的“皇族”、“伯爵”,他们也想努力构建一个时尚、充满个性的城市人形象,并且,渴望得到注视。
“就像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你,不再很卑微、渺小,而是勇敢的、张扬的。”罗福兴说。
采访间隙,罗福兴点了一支烟,橙红色的火光和酒店楼下的路灯,照亮了因为动迁已经变得空荡冷清的北京东路。这里曾是拍摄东方明珠的必选机位,罗福兴在采访前建议我们定一间高档酒店,比如,6300元一晚的W酒店,拍摄他和这次来帮他吹发型、第一次来上海的伙伴小天俯瞰东方明珠的镜头,他编排好了剧情:“一个连共享自行车都没骑过的人(指小天),你想象一下,这画面得多震撼,他估计会流泪吧”。
他不知道,开美发店之前,小天其实去过上海,在上海做过酒店保安和被套装卸员。但他知道,小天或他,仍是大城市的局外人。虽然他已不再像第一次来到深圳那样,为这车水马龙、大厦林立眼花缭乱,“我在拍摄的过程中,我看到路上好多人呢,这帮人密密麻麻的,跟工厂里面的员工似的,但他们都是去一些很牛的银行,很牛的企业。”
“但我也不羡慕,我觉得看着他们好难受。”他摇头,“如果要我跟他们一样,我会疯掉的。”
5月22日,结束一天拍摄,在一家地中海风格的快捷酒店,罗福兴擦掉深色口红与眼影,大口吞下品牌方给他点的外卖,一份上海本土连锁店的牛蛙饭。他收拾了一下桌上的铝箔盒子和塑料袋,点开小红书,看有没有新的商务邀约。
当天下午17点,他领了五千块。他打开账单明细,收入来自某国产品牌生发液,在另一个短视频平台,同样的“苍蝇蚊子进头发里都得开导航”的梗,为他带来了15000元的收入。
如今,包围着罗福兴的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流水线,取而代之的是快速更迭的流量。这曾是他看不上的东西,他历数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名字,觉得“太low了”,“我从来不刷短视频,要保护大脑。”
2018年,罗福兴在深圳开了一家名叫“皇妃”的理发店,仅维持了两三个月就倒闭了。2019年,他搭上互联网短视频风口的末班车,挤进竞争残酷的流量圈。起初,他签约过MCN机构(网红经纪公司),但他觉得公司分配的助理垄断了他的客户资源,不甘心其中百分之二三十的利益被抽取,“我两个助理都是寄生虫,什么用没有的。”
短视频的内容,一开始讲述个人经历和科普杀马特,到2022年,变成一套固定模式:配合电子舞曲,先展示一头清水挂面的湿发,接着,发型师一拉开围布,他变成另一个样子:顶着新创作的“炸裂”发型,命名为正人君子、一柱擎天,或者黑桃王子、蚌壳……接着,对着镜头摩挲头发,或是嘴唇。
商务合作陆续找上门来。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他,也有了一定自由。他挑选其中价格到位的,拼多多、七猫小说、探探……“都是挺下沉市场的那种”,价格实惠公道的不接,需求太麻烦的不接,“基本每个月拍两条视频,其余时间都在家打游戏,也能赚个几万块”。
他感觉有时候钱来得“跟大风刮似的”,但钱也是不可或缺的——在农村成绩名列前茅的大妹妹高考遭遇滑铁卢,自费读完技校后进厂里做会计,母亲心心念念地让他买房买车,稳定下来,也能让自己在村子里挣面子。
传播,或者操控流量,本也是罗福兴一直在做的事。杀马特发展初期,罗福兴找到网站和论坛,花几千块钱进行宣传:家族排行榜杀马特第一,杀马特排行榜罗福兴第一。他套用企业招商引资文案撰写软文和通稿,“怎么证明我们杀马特牛X?发软文,唬唬大众还是唬得了的。”
他注册了很多小号,模仿其他大贴吧里展开论战的话术,或是吹捧杀马特和罗福兴本人,或是进行攻击和批评,制造争论、提高话题度。现在回看,“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早期的互联网运营,好人也要扮,坏人也要扮,让好人同情我们,让坏人跟着做坏。”
抄袭网上其他公司的章程对杀马特“贵族”来管理,这是他的第二份工作。他为此去美发店做学徒,因为有更多的时间能打理群,也有专业免费的工具可以洗剪吹,他时不时在群里更新发型,“让大家都迷恋我、觉得我帅”。
“挣”来的流量,曾经带给他“做大哥的幻觉”,以及被簇拥的温暖。而今,站在广阔纷繁的流量世界,罗福兴常常是矛盾的。他想,自己是幸运的,没有按部就班地成为工厂里一颗温顺的螺丝钉。不同于从前,工厂的机器轰鸣声盖过杀马特群体向外呼喊的音量,短视频为他赢得更即时、更热闹的关注。现在,一条创作往往有几百万甚至更多的播放量,短视频推波助澜下,他进一步成为杀马特文化的符号象征。
罗福兴清楚,品牌商找上门是因为自己能做“量”,“可以把一个视频做到几千万播放量这样,几百万对我们来说都很劣质了。”但在流量的指挥棒下,他察觉到自己对做发型似乎已经不是纯粹的喜欢了。多数时候,他感觉头发离开身体,摆脱了地心引力。
他害怕自己成为工具,回到12岁时站在注胶机背后毫无话语权的自己。他渴望持续收割流量,却也对新的尝试充满不安全感。他提起,曾经有朋友劝他不要和艺术家合作办一些小展览:“你去了百分百被消费,玩完了就把你抛弃了。”
罗福兴还听说,有个叫庞麦郎的草根歌手走红后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,于是去看了几场庞麦郎出院后的带货直播。“我觉得他太被动了,我听别人说他思维有点混乱,在我的意识里有两种,一种是智商低,另一种是受到信息太多了,冲击太大了。”他点评,庞麦郎“完全就是一个工具”。
罗福兴没有意识到,自己站在一条新的流水线上,这条流水线规模同样庞大:全职主播规模以百万计,日活过亿;他只是感觉,这条流水线上的“产品”同样速朽:“很快速的消费,可能第二天流量就没了,要想新的了。”


 >
>